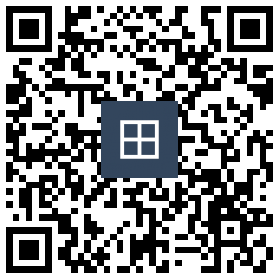二十八°·琐碎(八)
八·并非这里的世界意义何在
文/失意の栖居
母亲在冲着邻居家的狗恐吓几声无果后,担心犬吠吵得我无法入睡,特意过来替我掩上房门。我心怀感激,对母亲说:不妨事的,睡得着。入夜后,天幕宛若被一块巨大的黑布笼罩起来,再在黑布上散落地戳上数量不一的洞,漏下点点星光。人声偃旗息鼓,虫子们开始鸣叫起来,许是在觅食,或求偶,各种声音此起彼伏,给人声寂静的夜,奏起了交响乐。时不时地有几声犬吠传来,青蛙则从稻田、水沟、池塘、荷塘、草丛的各处,争先恐后地“呱呱”叫着。
乡下的夜,别有一番趣味。在外生活的年头——当然远比此刻呆着的地方生活时间长——一般我是从来不开窗睡觉的,街头的谩骂和吆喝声,建筑工地的机械声,车流的轰隆声,无一不是在制造噪音,那噪音,总勾起人心中的焦躁,惊扰人的睡眠。而此刻,远处的蛙声、近处的虫鸣声,穿过浓重的黑,穿过镂空的纱窗,丝丝缕缕,又绵延不断地飘进房来,让人觉得内心宁静——唯有心宁,方才听得真切、分明吧。我对母亲说不妨事,并非虚言。就在这恍恍惚惚里,不经意间,便堕进了梦乡。
翌日清晨,吃过早饭,闲来无事就在屋前屋后转悠。鸡舍里的鸡,早就出得笼来,悠哉悠哉地觅食着,我扔过去一把剩饭,鸡们就一哄而上。母亲说,多喂几只鸡,杀给你们吃。我问母亲,喂这么多,能卖钱不?母亲说,卖不了几个钱,买鸡仔的钱加上鸡吃的米,抵得上卖鸡的钱了。既然不挣钱就少喂几只鸡,省得劳神。我这样劝解道。“那可不行!逢年过节得杀鸡,你们回家得杀鸡,做人情也要用到鸡,外面的鸡哪有自己家养的好。”母亲断然拒绝。仓里有粮,地里有菜,笼里有鸡鸭,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是乡下人的本分和自信吧。我想大概。房子西侧的水杉,得有二十年了吧,还是不见有多粗壮,当时是想着等他们长大了能卖钱来着,东侧的一小片竹林,母亲想平了它做菜地,放了一把火,奈何竹子生命力旺盛,还剩一小半,在微风中窸窸窣窣地响着。母亲跟我说,今年有一户富贵人家,来家里砍了百十根竹子回去点缀自家的院子,因此挣了大几百块钱哩。竹子是好东西,可是放在我们家里,却不顶用。东侧的菜地里,今年多了几株树,一棵桃树,一棵板栗树,一株猕猴桃藤,还多了水缸大小的一池莲藕。桃树生长到第三年了,已经挂着三颗幼桃。我一一巡视着,想着再过些时候,就可以收获了,心里便美滋滋的。
太阳没有露面,有微风拂过,这在入夏的季节,算是蛮舒服的天气了,一两只白蝴蝶在半空中自由地飞舞着,几只小鸟儿也在树梢上跳来跳去,我注视它们的时间里,忽然觉得这样虚度光阴是一件何其惬意的事!索性我搬来一把老爷椅,放一本书在旁边,仰面躺着,自然地看天。毕竟是入夏时节,太阳将出未出,有一丝丝燥热。母亲说,你这傻小子,把椅子搬进屋来躺下呀,外面燥热着呢。我充耳不闻,也不反驳。天穹和天花板的区别,想必母亲是没有考虑在内的。我自然选择前者,些许燥热又算的了什么。小鸟儿唧唧咋咋地叫着,我注视着它们从水杉的一个枝头轻灵地跃到另一个枝头:起身时,快速地扑闪几下翅膀,加速到一定程度,舒展翅膀来一个优雅的滑翔,快要降落另一个枝头时,又抖动几下翅膀,完成减速后准确地伸足,抓住枝头,收翅。起承转合之间,似乎暗合某种至理,动作竟跟芭蕾舞的结束有着神似的地方。
叫声欢快,动作轻盈,想必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吧?“天上的飞鸟,它们既不耕种也不劳作,天父尚且养活它们,难道你不比它们更宝贵吗?”圣经·新约启示人们:满怀期待,放弃焦虑,及时行乐。但是人们啊,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执念所驭使着,被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包裹着,怕是离自由甚远吧。或许从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开始,有了思想,分了善恶,就有了烦恼吧。当人们开始仰望星空的时候,便有了翅膀,和罪恶。
什么是自由呢?终日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老父,自由吗?路口小卖部的店家,门庭若市忙忙碌碌赚得盆满钵满的,那是自由吗?吃喝玩乐,呼朋唤友,那是自由吗?村头那个干了一辈子木匠活,整天摆弄锯子、锉刀、刨子、墨斗的寡言少语的老木匠,他自由吗?驰骋商场、腰缠万贯、一掷千金,那便是自由吗?什么是自由,这是一个玄妙的问题:当你浑浑噩噩,心为形役的时候,你不是自由的;当你谈论它,纠结于它,执拗于它的时候,你多半也不是自由的;当你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沉浸在某种安定和专注之中的时候,你大概是自由的;当你超然物外,以觉察者的身份看待它,享受它的时候,你是自由的。有位禅师曾经这样解释:知足,就是知足而足,知道自己的脚迈向哪里,并因此而满足。方丈的距离和空间足以,何必忧虑和计较时空上更悠远的事?这大抵便是自由的至简的奥义吧。自由,需要际遇、秉性和智慧,不可多得。而那只翩翩起舞的白蝴蝶,它什么都没有,却是自由的。
胡思乱想过后,我摊开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页码读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天空突然漆黑如墨,一声惊雷,我道不好,赶紧收了躺椅。比豆还大的雨滴急速地砸向地面,迅速化开成一元硬币大小的雨痕,被水泥地吸收。须臾之间,门前的水泥地面完全湿透,雨下得更急,像一群愤怒的子弹,粗暴地冲向地面,“啪啪”地绽开的声音,让人仿佛能感受到地面的疼痛。房顶的雨水汇聚到手臂粗的出水管口,倾盆而下,好不热烈。我定定地站着,看雨,听雨。四季之雨,各有千秋。春雨,淅淅沥沥,润物无声,空气里带着冬去时的丝丝寒意和春的绵绵温暖;夏雨,酣畅淋漓,那是一种宣泄和释放,体内的浑浊,仿佛经过一场夏雨便能冲刷得干干净净;秋雨,雨打梧桐,萧瑟静谧,雨水从檐角滴落进破口瓦罐,“哒——哒”地诉说着渺远的思念。
雨下了一整天,一直到傍晚才结束。鸭子从笼里腆着肚子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像巡逻似的在水坑里觅食着,竹林被风一吹,雨抖落一地,莲池的荷叶上,顽强地挂着几滴晶莹的圆滚滚的水珠,一只蜗牛粘在上面一动不动,触角一碰,便飞快地缩进蜗牛壳里,那速度比顽皮的小孩伸手去摸烤得滚烫的地瓜被措不及防地烫到手还要快。矮墙那边的树上,绽开了好几朵洁白的栀子花,在将黑未黑的傍晚反射的白光让它特别显眼,微风送来它沁人的清香——就是它!中意它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不管何时,何处,见到它和闻到它的花香,总是莫名的激动。其原由不得而知,那种情愫也不想去深究。
不多久,天空浮现一轮月亮,没有星光。注视夜空月亮的那会,眼前一片朦胧,揉了揉眼睛,月亮竟然一分为二,一大一小两个月亮挂在夜空。
“并非这里的世界,意义何在?”我听到夜雨在耳边轻声说。
文/失意の栖居
母亲在冲着邻居家的狗恐吓几声无果后,担心犬吠吵得我无法入睡,特意过来替我掩上房门。我心怀感激,对母亲说:不妨事的,睡得着。入夜后,天幕宛若被一块巨大的黑布笼罩起来,再在黑布上散落地戳上数量不一的洞,漏下点点星光。人声偃旗息鼓,虫子们开始鸣叫起来,许是在觅食,或求偶,各种声音此起彼伏,给人声寂静的夜,奏起了交响乐。时不时地有几声犬吠传来,青蛙则从稻田、水沟、池塘、荷塘、草丛的各处,争先恐后地“呱呱”叫着。
乡下的夜,别有一番趣味。在外生活的年头——当然远比此刻呆着的地方生活时间长——一般我是从来不开窗睡觉的,街头的谩骂和吆喝声,建筑工地的机械声,车流的轰隆声,无一不是在制造噪音,那噪音,总勾起人心中的焦躁,惊扰人的睡眠。而此刻,远处的蛙声、近处的虫鸣声,穿过浓重的黑,穿过镂空的纱窗,丝丝缕缕,又绵延不断地飘进房来,让人觉得内心宁静——唯有心宁,方才听得真切、分明吧。我对母亲说不妨事,并非虚言。就在这恍恍惚惚里,不经意间,便堕进了梦乡。
翌日清晨,吃过早饭,闲来无事就在屋前屋后转悠。鸡舍里的鸡,早就出得笼来,悠哉悠哉地觅食着,我扔过去一把剩饭,鸡们就一哄而上。母亲说,多喂几只鸡,杀给你们吃。我问母亲,喂这么多,能卖钱不?母亲说,卖不了几个钱,买鸡仔的钱加上鸡吃的米,抵得上卖鸡的钱了。既然不挣钱就少喂几只鸡,省得劳神。我这样劝解道。“那可不行!逢年过节得杀鸡,你们回家得杀鸡,做人情也要用到鸡,外面的鸡哪有自己家养的好。”母亲断然拒绝。仓里有粮,地里有菜,笼里有鸡鸭,自食其力,自给自足,这是乡下人的本分和自信吧。我想大概。房子西侧的水杉,得有二十年了吧,还是不见有多粗壮,当时是想着等他们长大了能卖钱来着,东侧的一小片竹林,母亲想平了它做菜地,放了一把火,奈何竹子生命力旺盛,还剩一小半,在微风中窸窸窣窣地响着。母亲跟我说,今年有一户富贵人家,来家里砍了百十根竹子回去点缀自家的院子,因此挣了大几百块钱哩。竹子是好东西,可是放在我们家里,却不顶用。东侧的菜地里,今年多了几株树,一棵桃树,一棵板栗树,一株猕猴桃藤,还多了水缸大小的一池莲藕。桃树生长到第三年了,已经挂着三颗幼桃。我一一巡视着,想着再过些时候,就可以收获了,心里便美滋滋的。
太阳没有露面,有微风拂过,这在入夏的季节,算是蛮舒服的天气了,一两只白蝴蝶在半空中自由地飞舞着,几只小鸟儿也在树梢上跳来跳去,我注视它们的时间里,忽然觉得这样虚度光阴是一件何其惬意的事!索性我搬来一把老爷椅,放一本书在旁边,仰面躺着,自然地看天。毕竟是入夏时节,太阳将出未出,有一丝丝燥热。母亲说,你这傻小子,把椅子搬进屋来躺下呀,外面燥热着呢。我充耳不闻,也不反驳。天穹和天花板的区别,想必母亲是没有考虑在内的。我自然选择前者,些许燥热又算的了什么。小鸟儿唧唧咋咋地叫着,我注视着它们从水杉的一个枝头轻灵地跃到另一个枝头:起身时,快速地扑闪几下翅膀,加速到一定程度,舒展翅膀来一个优雅的滑翔,快要降落另一个枝头时,又抖动几下翅膀,完成减速后准确地伸足,抓住枝头,收翅。起承转合之间,似乎暗合某种至理,动作竟跟芭蕾舞的结束有着神似的地方。
叫声欢快,动作轻盈,想必是无忧无虑,自由自在的吧?“天上的飞鸟,它们既不耕种也不劳作,天父尚且养活它们,难道你不比它们更宝贵吗?”圣经·新约启示人们:满怀期待,放弃焦虑,及时行乐。但是人们啊,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执念所驭使着,被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包裹着,怕是离自由甚远吧。或许从亚当和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开始,有了思想,分了善恶,就有了烦恼吧。当人们开始仰望星空的时候,便有了翅膀,和罪恶。
什么是自由呢?终日起早贪黑,勤勤恳恳的老父,自由吗?路口小卖部的店家,门庭若市忙忙碌碌赚得盆满钵满的,那是自由吗?吃喝玩乐,呼朋唤友,那是自由吗?村头那个干了一辈子木匠活,整天摆弄锯子、锉刀、刨子、墨斗的寡言少语的老木匠,他自由吗?驰骋商场、腰缠万贯、一掷千金,那便是自由吗?什么是自由,这是一个玄妙的问题:当你浑浑噩噩,心为形役的时候,你不是自由的;当你谈论它,纠结于它,执拗于它的时候,你多半也不是自由的;当你察觉不到它的存在,沉浸在某种安定和专注之中的时候,你大概是自由的;当你超然物外,以觉察者的身份看待它,享受它的时候,你是自由的。有位禅师曾经这样解释:知足,就是知足而足,知道自己的脚迈向哪里,并因此而满足。方丈的距离和空间足以,何必忧虑和计较时空上更悠远的事?这大抵便是自由的至简的奥义吧。自由,需要际遇、秉性和智慧,不可多得。而那只翩翩起舞的白蝴蝶,它什么都没有,却是自由的。
胡思乱想过后,我摊开书,翻到夹着书签的页码读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天空突然漆黑如墨,一声惊雷,我道不好,赶紧收了躺椅。比豆还大的雨滴急速地砸向地面,迅速化开成一元硬币大小的雨痕,被水泥地吸收。须臾之间,门前的水泥地面完全湿透,雨下得更急,像一群愤怒的子弹,粗暴地冲向地面,“啪啪”地绽开的声音,让人仿佛能感受到地面的疼痛。房顶的雨水汇聚到手臂粗的出水管口,倾盆而下,好不热烈。我定定地站着,看雨,听雨。四季之雨,各有千秋。春雨,淅淅沥沥,润物无声,空气里带着冬去时的丝丝寒意和春的绵绵温暖;夏雨,酣畅淋漓,那是一种宣泄和释放,体内的浑浊,仿佛经过一场夏雨便能冲刷得干干净净;秋雨,雨打梧桐,萧瑟静谧,雨水从檐角滴落进破口瓦罐,“哒——哒”地诉说着渺远的思念。
雨下了一整天,一直到傍晚才结束。鸭子从笼里腆着肚子摇摇摆摆地走出来,像巡逻似的在水坑里觅食着,竹林被风一吹,雨抖落一地,莲池的荷叶上,顽强地挂着几滴晶莹的圆滚滚的水珠,一只蜗牛粘在上面一动不动,触角一碰,便飞快地缩进蜗牛壳里,那速度比顽皮的小孩伸手去摸烤得滚烫的地瓜被措不及防地烫到手还要快。矮墙那边的树上,绽开了好几朵洁白的栀子花,在将黑未黑的傍晚反射的白光让它特别显眼,微风送来它沁人的清香——就是它!中意它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不管何时,何处,见到它和闻到它的花香,总是莫名的激动。其原由不得而知,那种情愫也不想去深究。
不多久,天空浮现一轮月亮,没有星光。注视夜空月亮的那会,眼前一片朦胧,揉了揉眼睛,月亮竟然一分为二,一大一小两个月亮挂在夜空。
“并非这里的世界,意义何在?”我听到夜雨在耳边轻声说。
评论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