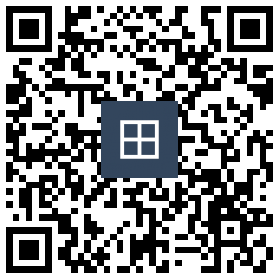二十八°·琐碎(零)
零·且听风吟
文/失意の栖居
六十公分见方的咖啡桌。左侧靠墙台,是一盏亮铜色金属制底座和柄的钨丝灯,发出即便是在白天,若要用来读书,也才堪堪够用的柔弱橘黄色的光。说是钨丝灯,也不尽然。我低头面朝上往灯罩里探去,只是构造有如钨丝灯,灯泡是不透明的白色,而灯罩是镶嵌玻璃珠的带花纹的贝壳状拼接的塑料制品,灯丝、灯泡、灯罩的加成,才得以营造一种类似静谧、温煦、心安的氛围。盛水的玻璃杯,自下而上,呈现碧绿、淡绿到几近透明的渐变,服务员添上热水后,飘出丝丝柠檬香。设计是一件奇妙的手艺。没有多少高深莫测的东西,不过是简单物什的裁剪、拼接,却能抓住人在精神层面普遍希求的某些东西。
我读到公园前7~6世纪的自然哲学派,提到最早的探究自然循环和变化的泰利斯、安纳克西曼德、安那西梅尼斯的出处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在哪里呢,脑海依稀熟悉这一名字。好在今天有大把的时间,于是打开笔记本的地图查起来。原来是黑海和地中海接壤,今土耳其一带。读了会苏菲的世界,简单地划了一些笔记,我又翻出刺杀骑士团长读起来。“你像是理解事物比一般人花时间的那一类型。不过从长远眼光看,时间大约在你这边。”村上一如既往地,在稀松平常的琐碎叙事中,毫无违和感地传达某种真知灼见和温情。我爱极了这种拾遗般的惊喜和醍醐般的满足。读他的书,就像在某个和煦的午后,在阳光洒满海面的大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寻觅,听海浪,听风,总能在某一处,邂逅精致的贝壳,珍稀的珠宝。我断定村上有某种天赋才能。或许我也有某种天赋才能也未可知。然而迄今为止,这种才能为何物,既未被自己发现,也未被他人告知。
音乐在缓缓的流淌。我闭目,仿佛置身于清新怡然的林间小溪旁,时间如汩汩的溪水缓缓流淌。对!忘掉琐碎生活中的一切冲突与不安。这一刻,时间是自由的,空气是自由的,大脑是自由的,手指头是自由的。这种感觉委实妙不可言,比之熬夜解决工作上的棘手难题或者赶工作进度——虽然这也不失为一种历练,或可获得某种类似成就感的东西——要胜过不知凡几。就情感而言,确是这样无疑。因为忙碌的工作充斥,使得我几乎没法记得哪怕是昨天都做了些什么——大抵大脑判断发生的一切乏善可陈,直接弃之或者扔在不知名的某处吧。而这个午后,这样的触感,鲜明而空灵,想必是大脑中意的一类东西。这般散漫地思来想去之际,困意如清凉的早晨的细微潮水般缓缓爬过来,眼帘也像有侍女放下窗帘般,一点点失去光亮、清晰,意识渐次沉入黑暗、虚无。
唤我醒来的,是一对男女的高谈阔论,音乐不知怎的也停了。因为中年男子的声音在这间还算安静的咖啡店颇为肆无忌惮,我伸出脖子隔着镂空的木墙看过去,男子振振有声,吐出“核心技术”、“国际上”等词,不时打着手势给自己的表达加上重点符,女子对面而坐,披肩黑发,微卷,正襟而坐又不显得拘谨和严肃,双目凝视对面的男子又噙着微笑,不时低头在小本子上记上几句。从这些线索判断,像是记者编辑之类的在对某高级工程师、优秀学者教授、知名企业家作某种采访。咖啡店聊工作,无可厚非嘛。聊工作者有之,聊家常者有之,伏案学习者有之,默默打游戏看电视者也有之,独自一人感受时间缓步流走的触感者——即我个人——也有之。有年轻活力的学生,有事业有成的前辈,有从容优雅的女性,下意识地,竟生出一分比较之意,而且似乎败下阵来。旋即又释然,一念生一念又很快熄灭。过去有那么一年,我直面内心,认真与之对话,已经将体内的某个魔鬼清除出体外,内心的藩篱拔倒了一大片,从此天广地阔。残存的魔鬼的阴影虽然偶有骚扰,但他想再钻进体内,却是不可能了。左右不过是一些念头罢了,头脑保持清明,那么魔鬼的念头也无伤大雅。谁的体内没有住着一两个魔鬼呢?“你无法成为自身之外的任何什么。”乌鸦的声音在脑海响起。
村上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在做什么呢?他已经早早的结了婚有了妻。他或许正在自己刚开张的酒吧里忙里忙外呢。兴许此刻正在调酒呢。再晚些时候,或许他在客人离去,打烊后不无辛苦地擦拭桌面、擦拭酒杯吧——放着我一窍不通的古典唱片。“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恰如也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再不久,他开始写小说。且听风吟,以悲伤开始。
文/失意の栖居
六十公分见方的咖啡桌。左侧靠墙台,是一盏亮铜色金属制底座和柄的钨丝灯,发出即便是在白天,若要用来读书,也才堪堪够用的柔弱橘黄色的光。说是钨丝灯,也不尽然。我低头面朝上往灯罩里探去,只是构造有如钨丝灯,灯泡是不透明的白色,而灯罩是镶嵌玻璃珠的带花纹的贝壳状拼接的塑料制品,灯丝、灯泡、灯罩的加成,才得以营造一种类似静谧、温煦、心安的氛围。盛水的玻璃杯,自下而上,呈现碧绿、淡绿到几近透明的渐变,服务员添上热水后,飘出丝丝柠檬香。设计是一件奇妙的手艺。没有多少高深莫测的东西,不过是简单物什的裁剪、拼接,却能抓住人在精神层面普遍希求的某些东西。
我读到公园前7~6世纪的自然哲学派,提到最早的探究自然循环和变化的泰利斯、安纳克西曼德、安那西梅尼斯的出处小亚细亚。小亚细亚在哪里呢,脑海依稀熟悉这一名字。好在今天有大把的时间,于是打开笔记本的地图查起来。原来是黑海和地中海接壤,今土耳其一带。读了会苏菲的世界,简单地划了一些笔记,我又翻出刺杀骑士团长读起来。“你像是理解事物比一般人花时间的那一类型。不过从长远眼光看,时间大约在你这边。”村上一如既往地,在稀松平常的琐碎叙事中,毫无违和感地传达某种真知灼见和温情。我爱极了这种拾遗般的惊喜和醍醐般的满足。读他的书,就像在某个和煦的午后,在阳光洒满海面的大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行走,寻觅,听海浪,听风,总能在某一处,邂逅精致的贝壳,珍稀的珠宝。我断定村上有某种天赋才能。或许我也有某种天赋才能也未可知。然而迄今为止,这种才能为何物,既未被自己发现,也未被他人告知。
音乐在缓缓的流淌。我闭目,仿佛置身于清新怡然的林间小溪旁,时间如汩汩的溪水缓缓流淌。对!忘掉琐碎生活中的一切冲突与不安。这一刻,时间是自由的,空气是自由的,大脑是自由的,手指头是自由的。这种感觉委实妙不可言,比之熬夜解决工作上的棘手难题或者赶工作进度——虽然这也不失为一种历练,或可获得某种类似成就感的东西——要胜过不知凡几。就情感而言,确是这样无疑。因为忙碌的工作充斥,使得我几乎没法记得哪怕是昨天都做了些什么——大抵大脑判断发生的一切乏善可陈,直接弃之或者扔在不知名的某处吧。而这个午后,这样的触感,鲜明而空灵,想必是大脑中意的一类东西。这般散漫地思来想去之际,困意如清凉的早晨的细微潮水般缓缓爬过来,眼帘也像有侍女放下窗帘般,一点点失去光亮、清晰,意识渐次沉入黑暗、虚无。
唤我醒来的,是一对男女的高谈阔论,音乐不知怎的也停了。因为中年男子的声音在这间还算安静的咖啡店颇为肆无忌惮,我伸出脖子隔着镂空的木墙看过去,男子振振有声,吐出“核心技术”、“国际上”等词,不时打着手势给自己的表达加上重点符,女子对面而坐,披肩黑发,微卷,正襟而坐又不显得拘谨和严肃,双目凝视对面的男子又噙着微笑,不时低头在小本子上记上几句。从这些线索判断,像是记者编辑之类的在对某高级工程师、优秀学者教授、知名企业家作某种采访。咖啡店聊工作,无可厚非嘛。聊工作者有之,聊家常者有之,伏案学习者有之,默默打游戏看电视者也有之,独自一人感受时间缓步流走的触感者——即我个人——也有之。有年轻活力的学生,有事业有成的前辈,有从容优雅的女性,下意识地,竟生出一分比较之意,而且似乎败下阵来。旋即又释然,一念生一念又很快熄灭。过去有那么一年,我直面内心,认真与之对话,已经将体内的某个魔鬼清除出体外,内心的藩篱拔倒了一大片,从此天广地阔。残存的魔鬼的阴影虽然偶有骚扰,但他想再钻进体内,却是不可能了。左右不过是一些念头罢了,头脑保持清明,那么魔鬼的念头也无伤大雅。谁的体内没有住着一两个魔鬼呢?“你无法成为自身之外的任何什么。”乌鸦的声音在脑海响起。
村上在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在做什么呢?他已经早早的结了婚有了妻。他或许正在自己刚开张的酒吧里忙里忙外呢。兴许此刻正在调酒呢。再晚些时候,或许他在客人离去,打烊后不无辛苦地擦拭桌面、擦拭酒杯吧——放着我一窍不通的古典唱片。“世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章,恰如也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再不久,他开始写小说。且听风吟,以悲伤开始。
评论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