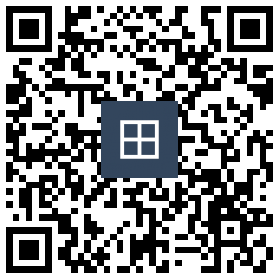父亲
一
西林渡口,车辆顺着河堤蜿蜒排了百十米长,轮渡一次只能渡十来辆车,又有不守规矩的司机加塞。我们时间紧吧得很,于是决定把车停在河这边,人过得河去,让父亲来接我们一趟。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说明缘由,父亲连声说“好,我十分钟后就到。”
我携妻和闺女过了河,稍顷,远远瞧见一辆红色的、“嘟嘟嘟”喘气儿的摩托三轮车慢吞吞驶过来。其实我目力不好,但我知道分明就是父亲来了——人很多时候是靠感觉在判断。有时候,你对一样东西很熟悉,可能是因为朝夕相处,或者耳濡目染,亦或者思念。我和妻与父亲打过招呼,钻进了三轮车。父亲在前面开车,有一搭没一搭与我们寒暄。车里发动机声很吵,我看着父亲微弓的背,有些蓬乱的、夹着不少银丝的头发,棕黑色的手臂,粗糙的手背,想象他握着车把的,满是老茧和伤口的手,就莫名伤感起来,就想写一写父亲。
二
这条河,资江的支流,围住了我的家。来到此岸,便回到家,回到那个草木砂石都觉得亲切的、不同于“别处”的地方;去得彼岸,我便是那漂泊的游子,天地一沙鸥。这条河,我淌过了有十五载了。乡镇交通不方便,多年来打这里出门或回家,一直是父亲在接送。
早些年念书的时候,出门总是母亲在打点行李,父亲默默等着,等收拾妥当就发动他那辆摩托车,载我出门。生活上父亲叮咛得不多,学业上他也不过于担心,一路总是无话。到了河边,有时候船未到,便陪我等船,等我上船,他便离开。后来工作了,他会多叮嘱我几句,说工作要动脑筋,要多交朋友,要识人留心眼云云。回家也每每是父亲接送,他整天忙碌个不停,接我的时候总是不修边幅的模样,一眼就可以瞧出他是在做着什么活计抽空过来的。他载我到家后,便又马不停蹄地出门了。很少见他有时间悠哉地抽上一支烟,和我交谈一番——十数年来,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这种几率就更小了。
迎来送往的寒暑岁月里,有两次我印象很深。一次是高中毕业回家,父亲照例去渡口接我。毕业带回的东西比较多,除了衣物外还有一些书籍,老旧的皮箱装了满满一箱。车轱辘不好使,有段路不好走,行李搬运起来颇不方便。父亲便执意过得河去,在车站等我。一个箱子我自是也能应付的,但远不如父亲那般轻松,他扛起箱子在前面引路,上得河堤,又下得河堤。大概是那一次,父亲弯弯的背影印在了脑海。另一次,是同年去魔都念大学。父亲与我同去。我们挤在学校宿舍的硬板床上对付了一宿,次日傍晚,父亲便要折返,我去火车站送他。我凝视他进了闸机的背影,怔怔地想:这个沉默的男人在两日内风尘仆仆地,跨过数个省,1000多公里,所求者何?所希冀者何?外滩的驻足,看着浑浊翻涌的江水,黄浦江的江风,是否在他心底吹起一丝涟漪?犹记得他时常在临别和电话里说的那句:需要钱就只管讲,钱不是问题。铿锵有力。
三
钱不是问题。是一个父亲的担当,但在一般的农村人家里,却绝不是事实。九八年,我家的老房子墙体裂开严重,不能住人了,咬着牙盖新房子。据我母亲说,当时我家里只剩下五块钱了。盖房子用的材料费、人工费,是赊的、借的、欠的。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都要还盖房子的钱。早些年,农村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到了年二十七八,二十八九,就会有人上你家门,或者你家家长去别家串门。一般是聊家长里短,以“唉,你吃饭了没”,“来,抽根烟”打开话匣子。实际上是接近年关了,家家户户要把借款收回来,或者还钱给人家。能收回多少款,能还上多少,大家都乐意接受,表面和和气气的,算是对过年的敬意。这时节,忙碌了一年的父亲也要上别家送钱,或者收账。也有些人不体面,三番五次上门收账都只推脱,铁公鸡不拔毛,这时候父亲往往会挨母亲一顿数落,甚至拌嘴几句。上门讨债,找父亲结算工钱的,每年年关都有。逢此时,母亲忙着招待,父亲默默去拿记账本和钱。如此光景,使我神色黯然。以我十多岁的眼光,便看出了父亲母亲操持一家,殊为不易。
何止是我的父亲母亲不容易,我看到的乡邻的其他父亲母亲莫不如是。零八年夏,七旬的祖父、父亲、我祖孙三人在田间休息,四野全是稻田,空旷无垠,却没有一丝风,头顶是灼灼烈日,我摇着草帽,任汗水在脸颊、脊背各处驰骋。周围是或远或近的轰隆的打稻机声,我在想:我的父亲母亲,我的乡邻,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何其辛苦!他们养育孩子是多么不容易!他们没有知识,没有平台,没有贵人,但有着坚毅隐忍的心性和家的担当!父亲这一辈,他们的父辈从战争和饥荒年代过来,大多一贫如洗,等他们长大时,高考刚刚恢复,改革开放也才喊口号,他们无从受惠,辛劳一生。他们像那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这个家。
蜡烛是不会心疼自己的,但是得到光和温暖的人会。
四
父亲是有遗憾的。父亲很聪慧,念书的时候,远超同侪(父亲自己这样认为),奈何家境窘困,只到高中便无以为继。“如果当年家里能够继续供我念书,那上大学是十拿九稳的,那现在不说做大官,至少也是衣食无忧了。”这是父亲原话。说起当年辍学,父亲总是唏嘘。鲜衣怒马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父亲确实头脑灵活。家里盖房子多亏了父亲有样学样,砌墙,粉刷,排线,贴砖,他都能自己来,也省了不少工钱。家里电出了问题,别家需要找电工来看,他自己动手:拉闸,用试电笔检测线路,接线等。我小时候对这些也感兴趣,经常跟着他跑。有时候提醒他小心点,他不以为意地说:没事,你只要搞清楚了零线,火线,就不会有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比如你妈,人蠢就怎么教她也不会。父亲算数,记忆也是不错的,他会找规律进行计算和记忆。有时候便要炫耀他的聪明。他又好学,二维码刚出来那会,他觉得二维码很神奇,便要问我二维码怎么回事。买了个智能手机,便要琢磨微信各种功能怎么用,怎么上网查资料。我一回家,他总有几个问题攒在那里要问我。我演示给他看一遍,他便固执地要自己实操几遍,记下来或理解了,心满意足地说:原来如此,也蛮简单的。顺带又鄙视母亲一顿。看他高兴了,我也开心。
任谁经常鄙视你,你也不会喜欢的。所以母亲很不喜欢父亲的自大和夸夸其谈。父亲喜欢在我面前说,我揣测大概有几种原因:父亲觉得我与他是一类人,聪明人,有种惺惺相惜,也有种优越感流露。或者父亲想获得我的赞扬。客观地讲,我也不大喜欢父亲的自吹自擂。父亲喜欢露锋,我则不然,喜欢藏拙。况且他说的那些东西也委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大肆炫耀。不过大抵这是他的乐趣,我也乐得成全。可是有一回,忘记了因为什么,我不耐烦了。我对父亲说,我掌握的知识百倍于你,不要在我面前炫耀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大概这话深深伤害了他,他多次提起我说过这话,久久无法释怀。但他仍然热衷于学知识,总是把“活到老,学不老,要与时俱进”挂在嘴边。
早年我念书尚可。乡邻歆羡,亲朋赞誉,老师青睐,一路风光走进了大学,保送了研究生。父亲脸上也有光。父亲的遗憾,大抵由我稍微弥补了一些吧。只不过人生际遇万千,我不出息,混得也极为平庸。就结果而言,想必不那么符合父亲的心意吧。不过父亲不说破。
五
我很早便离开父母外出求学,与家人一直聚少离多。所以在家的时候,母亲总要想方设法给我做一些好吃的,买一些好吃的。这时候,父亲便是那个采买的坚定执行者。比如谁家捕鱼,谁家屠狗,母亲闻讯,便对父亲发号施令,父亲便默默去一一买过来。有个头疼感冒,母亲总是一顿唠叨,父亲则把药买回来拿到我面前,有时附带责备几句。我要个什么东西,要办个什么事,跟父亲讲,他总能想办法把东西取来,把事办成。父亲做的一切,不言不语,不争不抢。一般来讲,母爱柔情似水,细腻,贴心,难免充满溺爱。而父爱,总如山。在一个家里,父亲肩负家的责任,要庇护妻儿,他需要理智、坚毅。父亲的爱,不如母亲热情,但却厚重,让人感到踏实。
父亲老了。岁月和生活染白了他的发丝,在他额头犁出一道道皱纹,也把他的身形压得更弯、更小。病痛,也像债主一般找上了他。
父亲老了。因为他变得更唠叨了,慈爱了,温柔了。他开始主动约我的时间,跟我聊一个多小时,关心我是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他在抱着孙女、和孙女视频的时候,脸上笑开了花——以前我从未见过父亲这样笑。迁户口时,我托父亲帮我去派出所办迁出,大概是安土重迁或是别的什么原因,父亲有点反对,最后还是答应下来。我要的比较着急,父亲在电话的第二天便帮我去办迁出。不料父亲去镇上邮寄的时候,从县里来的快递员揽件刚走,要等好几天才会再过来。“你着急用的话,我现在搭汽车去县城,把材料送到快递员手里”父亲极其平淡、自然地说。我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鼻子不争气地一酸,话也变得哽咽。我脑海中是父亲的身影、眼神。这个男人,这个老头,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温柔,如此苍老了呢。我别过脸,仰起头,把眼眶里氤氲的泪雾吸走。
六
我们只在家小坐了一会,便不得不出发了。父亲依旧开着他那辆大喘气的三轮摩托车送我们去渡口。
“嘟嘟嘟”的发动机声回荡在耳边,我总是在行走的路上莫可名状地伤感……
西林渡口,车辆顺着河堤蜿蜒排了百十米长,轮渡一次只能渡十来辆车,又有不守规矩的司机加塞。我们时间紧吧得很,于是决定把车停在河这边,人过得河去,让父亲来接我们一趟。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说明缘由,父亲连声说“好,我十分钟后就到。”
我携妻和闺女过了河,稍顷,远远瞧见一辆红色的、“嘟嘟嘟”喘气儿的摩托三轮车慢吞吞驶过来。其实我目力不好,但我知道分明就是父亲来了——人很多时候是靠感觉在判断。有时候,你对一样东西很熟悉,可能是因为朝夕相处,或者耳濡目染,亦或者思念。我和妻与父亲打过招呼,钻进了三轮车。父亲在前面开车,有一搭没一搭与我们寒暄。车里发动机声很吵,我看着父亲微弓的背,有些蓬乱的、夹着不少银丝的头发,棕黑色的手臂,粗糙的手背,想象他握着车把的,满是老茧和伤口的手,就莫名伤感起来,就想写一写父亲。
二
这条河,资江的支流,围住了我的家。来到此岸,便回到家,回到那个草木砂石都觉得亲切的、不同于“别处”的地方;去得彼岸,我便是那漂泊的游子,天地一沙鸥。这条河,我淌过了有十五载了。乡镇交通不方便,多年来打这里出门或回家,一直是父亲在接送。
早些年念书的时候,出门总是母亲在打点行李,父亲默默等着,等收拾妥当就发动他那辆摩托车,载我出门。生活上父亲叮咛得不多,学业上他也不过于担心,一路总是无话。到了河边,有时候船未到,便陪我等船,等我上船,他便离开。后来工作了,他会多叮嘱我几句,说工作要动脑筋,要多交朋友,要识人留心眼云云。回家也每每是父亲接送,他整天忙碌个不停,接我的时候总是不修边幅的模样,一眼就可以瞧出他是在做着什么活计抽空过来的。他载我到家后,便又马不停蹄地出门了。很少见他有时间悠哉地抽上一支烟,和我交谈一番——十数年来,我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这种几率就更小了。
迎来送往的寒暑岁月里,有两次我印象很深。一次是高中毕业回家,父亲照例去渡口接我。毕业带回的东西比较多,除了衣物外还有一些书籍,老旧的皮箱装了满满一箱。车轱辘不好使,有段路不好走,行李搬运起来颇不方便。父亲便执意过得河去,在车站等我。一个箱子我自是也能应付的,但远不如父亲那般轻松,他扛起箱子在前面引路,上得河堤,又下得河堤。大概是那一次,父亲弯弯的背影印在了脑海。另一次,是同年去魔都念大学。父亲与我同去。我们挤在学校宿舍的硬板床上对付了一宿,次日傍晚,父亲便要折返,我去火车站送他。我凝视他进了闸机的背影,怔怔地想:这个沉默的男人在两日内风尘仆仆地,跨过数个省,1000多公里,所求者何?所希冀者何?外滩的驻足,看着浑浊翻涌的江水,黄浦江的江风,是否在他心底吹起一丝涟漪?犹记得他时常在临别和电话里说的那句:需要钱就只管讲,钱不是问题。铿锵有力。
三
钱不是问题。是一个父亲的担当,但在一般的农村人家里,却绝不是事实。九八年,我家的老房子墙体裂开严重,不能住人了,咬着牙盖新房子。据我母亲说,当时我家里只剩下五块钱了。盖房子用的材料费、人工费,是赊的、借的、欠的。往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都要还盖房子的钱。早些年,农村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到了年二十七八,二十八九,就会有人上你家门,或者你家家长去别家串门。一般是聊家长里短,以“唉,你吃饭了没”,“来,抽根烟”打开话匣子。实际上是接近年关了,家家户户要把借款收回来,或者还钱给人家。能收回多少款,能还上多少,大家都乐意接受,表面和和气气的,算是对过年的敬意。这时节,忙碌了一年的父亲也要上别家送钱,或者收账。也有些人不体面,三番五次上门收账都只推脱,铁公鸡不拔毛,这时候父亲往往会挨母亲一顿数落,甚至拌嘴几句。上门讨债,找父亲结算工钱的,每年年关都有。逢此时,母亲忙着招待,父亲默默去拿记账本和钱。如此光景,使我神色黯然。以我十多岁的眼光,便看出了父亲母亲操持一家,殊为不易。
何止是我的父亲母亲不容易,我看到的乡邻的其他父亲母亲莫不如是。零八年夏,七旬的祖父、父亲、我祖孙三人在田间休息,四野全是稻田,空旷无垠,却没有一丝风,头顶是灼灼烈日,我摇着草帽,任汗水在脸颊、脊背各处驰骋。周围是或远或近的轰隆的打稻机声,我在想:我的父亲母亲,我的乡邻,这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何其辛苦!他们养育孩子是多么不容易!他们没有知识,没有平台,没有贵人,但有着坚毅隐忍的心性和家的担当!父亲这一辈,他们的父辈从战争和饥荒年代过来,大多一贫如洗,等他们长大时,高考刚刚恢复,改革开放也才喊口号,他们无从受惠,辛劳一生。他们像那蜡烛一样,燃烧了自己,照亮了这个家。
蜡烛是不会心疼自己的,但是得到光和温暖的人会。
四
父亲是有遗憾的。父亲很聪慧,念书的时候,远超同侪(父亲自己这样认为),奈何家境窘困,只到高中便无以为继。“如果当年家里能够继续供我念书,那上大学是十拿九稳的,那现在不说做大官,至少也是衣食无忧了。”这是父亲原话。说起当年辍学,父亲总是唏嘘。鲜衣怒马我是持怀疑态度的,不过父亲确实头脑灵活。家里盖房子多亏了父亲有样学样,砌墙,粉刷,排线,贴砖,他都能自己来,也省了不少工钱。家里电出了问题,别家需要找电工来看,他自己动手:拉闸,用试电笔检测线路,接线等。我小时候对这些也感兴趣,经常跟着他跑。有时候提醒他小心点,他不以为意地说:没事,你只要搞清楚了零线,火线,就不会有问题。其实很简单,但是对有些人来说——比如你妈,人蠢就怎么教她也不会。父亲算数,记忆也是不错的,他会找规律进行计算和记忆。有时候便要炫耀他的聪明。他又好学,二维码刚出来那会,他觉得二维码很神奇,便要问我二维码怎么回事。买了个智能手机,便要琢磨微信各种功能怎么用,怎么上网查资料。我一回家,他总有几个问题攒在那里要问我。我演示给他看一遍,他便固执地要自己实操几遍,记下来或理解了,心满意足地说:原来如此,也蛮简单的。顺带又鄙视母亲一顿。看他高兴了,我也开心。
任谁经常鄙视你,你也不会喜欢的。所以母亲很不喜欢父亲的自大和夸夸其谈。父亲喜欢在我面前说,我揣测大概有几种原因:父亲觉得我与他是一类人,聪明人,有种惺惺相惜,也有种优越感流露。或者父亲想获得我的赞扬。客观地讲,我也不大喜欢父亲的自吹自擂。父亲喜欢露锋,我则不然,喜欢藏拙。况且他说的那些东西也委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值得大肆炫耀。不过大抵这是他的乐趣,我也乐得成全。可是有一回,忘记了因为什么,我不耐烦了。我对父亲说,我掌握的知识百倍于你,不要在我面前炫耀了。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大概这话深深伤害了他,他多次提起我说过这话,久久无法释怀。但他仍然热衷于学知识,总是把“活到老,学不老,要与时俱进”挂在嘴边。
早年我念书尚可。乡邻歆羡,亲朋赞誉,老师青睐,一路风光走进了大学,保送了研究生。父亲脸上也有光。父亲的遗憾,大抵由我稍微弥补了一些吧。只不过人生际遇万千,我不出息,混得也极为平庸。就结果而言,想必不那么符合父亲的心意吧。不过父亲不说破。
五
我很早便离开父母外出求学,与家人一直聚少离多。所以在家的时候,母亲总要想方设法给我做一些好吃的,买一些好吃的。这时候,父亲便是那个采买的坚定执行者。比如谁家捕鱼,谁家屠狗,母亲闻讯,便对父亲发号施令,父亲便默默去一一买过来。有个头疼感冒,母亲总是一顿唠叨,父亲则把药买回来拿到我面前,有时附带责备几句。我要个什么东西,要办个什么事,跟父亲讲,他总能想办法把东西取来,把事办成。父亲做的一切,不言不语,不争不抢。一般来讲,母爱柔情似水,细腻,贴心,难免充满溺爱。而父爱,总如山。在一个家里,父亲肩负家的责任,要庇护妻儿,他需要理智、坚毅。父亲的爱,不如母亲热情,但却厚重,让人感到踏实。
父亲老了。岁月和生活染白了他的发丝,在他额头犁出一道道皱纹,也把他的身形压得更弯、更小。病痛,也像债主一般找上了他。
父亲老了。因为他变得更唠叨了,慈爱了,温柔了。他开始主动约我的时间,跟我聊一个多小时,关心我是否适应新的工作环境。他在抱着孙女、和孙女视频的时候,脸上笑开了花——以前我从未见过父亲这样笑。迁户口时,我托父亲帮我去派出所办迁出,大概是安土重迁或是别的什么原因,父亲有点反对,最后还是答应下来。我要的比较着急,父亲在电话的第二天便帮我去办迁出。不料父亲去镇上邮寄的时候,从县里来的快递员揽件刚走,要等好几天才会再过来。“你着急用的话,我现在搭汽车去县城,把材料送到快递员手里”父亲极其平淡、自然地说。我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鼻子不争气地一酸,话也变得哽咽。我脑海中是父亲的身影、眼神。这个男人,这个老头,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温柔,如此苍老了呢。我别过脸,仰起头,把眼眶里氤氲的泪雾吸走。
六
我们只在家小坐了一会,便不得不出发了。父亲依旧开着他那辆大喘气的三轮摩托车送我们去渡口。
“嘟嘟嘟”的发动机声回荡在耳边,我总是在行走的路上莫可名状地伤感……
评论
下一页